老树画画:把自己都放倒了,还能放不倒天下人?
来源:理想国imaginist
编者按:这是 12 月 6 日理想国的沙龙精选,谈话有部分涉及杨葵新书,如没有看过书,可能会有隔膜,但抛开这部分,三位嘉宾所聊“冷暖人生”,诸多亮点。这也是编者听得很认真的一场沙龙。
“你认为的别人怎么看你,和别人实际怎么看你,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当这个釜底之薪被抽掉,你就会想,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吧。这样一来,就诚恳了。大多数人第一念头想到的自由,都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其实跟“自由”恰巧是相反的。联系到现实生活,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当然这跟经济能力、吃喝拉撒都有关系。”——杨葵
“少年轻狂,总想得很大,其实自己下一顿吃什么都不能解决。同时,年轻的好玩、年轻的魅力也在于不知所以。生活就是平淡构成的,我们对阅读的期待,对于画的期待,包括对自己生活的期待,不要指望什么奇迹。现在都是耸人听闻,“快点看!不看就被删了!”微信上老有这个,你感觉活在一个传奇里。我觉得太扯淡了,太可笑了。人要不面对自己的羞耻,就会变得特别软弱。”——老树画画
写写画画,冷暖人生
杨葵、老树画画、陈晓楠
陈晓楠 :各位好!很少参加这样的活动,所以没什么经验。之前准备到很晚,后来发现还是想到哪聊到哪比较好。我跟杨葵在生活里是非常熟的朋友,他是我精神上的大表哥。我们这些人有了精神上的困惑特别爱找他,他是我们生活里一个永远淡定、明白的存在。他是我第一号闺密“亲生的哥”,她老说这是我亲哥,其实没有血缘关系。所以他也是我精神上的大表哥。
老树,著名画家,著名学者。我知道今天很多人是因为老树来的。我刚知道他和杨葵之前也没有见过,这个我还挺诧异的。杨葵的书,老树的画,让我觉得他们神交已久,是非常相似精神状态的人。这两个人是我所见过的真正文如其人、画如其人的状态。刚刚跟杨葵说,我今天之所以在这儿不紧张,是因为我想明白一件事——不能班门弄斧。不能跟杨葵谈写作,也不能跟老树谈画画,那谈什么呢?谈人生。所以杨葵给的这题目特别好:“写写画画,冷暖人生”。他就是一个特别周到体贴的全科人儿,为了让我不那么紧张,他说我们可以聊人生啊。
无论看杨葵的书还是看老树的画,似乎可以感觉到他们写字画画时候的状态,他们自有一种好像谁也打不动的耐心和节奏,这个节奏在当今时代,是需要有一份定力的。这两个中年老男人坐在面前,我就跟他们说,今天想探求一下老男人的心里秘密。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吧。
杨葵自己说过,年轻时写的东西和现在写的有很大差别。早年你有本书叫《在黑夜抽筋成长》,你也曾经是一个抽筋的人,这个我未曾得见,我认识你的时候已经是现在的模样了。你能谈谈你的人生节点么?什么东西的改变造成了你写作上的改变?
杨葵 :先说两句客气话。今天为我新书做活动,请到他们二位,我很惶恐也很兴奋。晓楠是好朋友,常在一起聚会,但从没这么正经聊过,刚才她说话时我都不太敢看她,我想她也有差不多的感觉。而且我印象中,晓楠从没参加过图书会活动,所以那天问她能不能来,我很冒昧,她也特别紧张,她说你们文化人都是怎么活动法儿?该怎么准备?我说都比较随意,你这么一认真我也得认真点。
再说树老师。原来跟树老师不认识,两年前在新浪微博看到他的画,特别高兴特别喜欢,有种知音的感觉。后来又发现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即便如此,我们今天是头一次见面,平常在微博上也互动很少,刚开始我还点个赞、竖个大拇指什么的,后来树老师太红了,每幅画下面都太多赞和大拇指了,我就不赞了,但是我相信,他知道我心里一直在点赞。
真的非常兴奋和惶恐……晓楠你刚才问的什么问题?一兴奋给忘了……
陈晓楠 :那我先从个人关注的一点问起,我觉得和你在这方面有一点交集,有的可聊——你那天跟我说,《百家姓》写大历史当中小人物个体的命运,我们节目也常年做这样的小人物、普通人的故事。对你来说,写这样的东西,要到什么样的程度,你才觉得这个人要写。生活中很多人物其实并没有什么戏剧力度。
我家小孩两岁多,现在特别爱说“突然”,给她讲故事,说讲完了,她说没有啊,没有“突然”啊。一般来说人都喜欢追求“突然”,包括我们节目做一个人物,如果没有足够多的“突然”,你就会想值不值得去做。但是我看你写的东西,很多像浮雕一样的人物,他们虽然没有那么多的“突然”和“非常”,但是常态下的有细节、留白的人物特别趋近于我们所接触到的世道人心的真相,所以特别可贵。这是我读你《百家姓》时心中一震的。
那么,到什么样的触动,或者是到什么样的份量,会觉得这个人是值得写的?或者说敢于提笔写?

杨葵 :我巨蟹座,据说就是特别细了吧唧的人,大事常常看不清,但是生活里的小事、细节会特别关注。你问这问题我又想到个细节:有年夏天,石康在我们家玩,我在阳台上站了会儿,跟他说,嘿!一股小风儿吹过,真舒服啊!他听了目瞪口呆,说夏天阳台上一股小风儿吹过……这有特么什么可说的啊。你看这就是人的趣味和性格各不相同,他喜欢磕大事儿,我关注小破事儿。
观察生活是随时随地的,包括对人的观察、对文字的观察。你问积攒到什么时候,回答是:到特别想写的时候。但要补充说明,这个“特别想写”并非一直刻意地去攒,可能就是一瞬间一个念头,你突然想写。一旦进入写流程,又需要考虑更多的事。
前些天和牟森聊了一次,牟老喜欢“架构”,他说《百家姓》是有架构的,这个我是承认的。我也不是只有细了吧唧的时候,《百家姓》隐含着大的架构,被牟老看出来了。
说到这里又想到,《百家姓》从第一版到现在,将近四年了,我还有个更隐秘的野心,一直没人说出来。很多人评论这本书,但就是始终没人击中那一点。没想到就在前几天,清华大学的格非教授,也是著名的作家,他给一个公众好写了个《百家姓》的推荐,我看得眼泪都要下来了——终于有人说出来了!他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用朴素的正念打量一个人,用最大的善意理解他们,他们的姿容和声影就会像浮云过目一样,平淡无奇而又自然真确。”就是这个。
很多人在网上说《百家姓》,说这不就是中学生作文嘛,白开水,没高潮。不好意思,这正是我想写的,还在追求糖水儿、高潮的人现在确实还看不懂,这也很正常。
你们看老树的画也是,特别简单,闲散,也没什么高潮。我们实际上是不好意思写那些、画那些“高潮”。
陈晓楠 :我记得有次《百家姓》的论坛上,有个读者提问,是不是写的这些人都太美化了。你当时的回答是:我没想到美化和丑化,我的思绪散漫开就想到了这些,这个人留在我印象里的就是这些。这是你体察这个世界的温度。我特别喜欢每一篇结尾的留白,那些人物从你笔下结束的这一刻,就走进了生活的洪流。每个人生命中的这些过客,都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有种生命力。你说他们生活里没有苦难?一定是有的,可不一定都是什么“突然”和“非常”,生活就是这样的。平常,反而让我感觉到一种生命力在里头。
刚才你讲到,老树的画也不会画一些高潮、裂变,听说老树当年也画过特艰涩的画,你把以前的画拿出来,大家都特惊讶是吗?和现在都不是一回事儿了。
老树 :还是说杨葵,我们是一个专业,都是学中文出身。我好多年没把自己当做一个学中文的了,今天一说把我的劲儿也聊起来了。他出这两本书,出版社找我给做一个封面图,就这么简单。我对杨葵老师是仰慕很久了,很早看到他在出版社做的书,非常喜欢。一直想见也没有缘分。还有晓楠,也老看她做的节目。我说一说《百家姓》,说一下我的理解,包括我的画。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就是跟岁数有关,年轻的时候装B,你看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本科生有一个毛病,写毕业论文的时候,那个开题报告,做标题,中国经济向何处去。李克强都搞不明白的事儿是你能写的吗?少年轻狂,总想得很大,其实自己下一顿吃什么都不能解决。同时,年轻的好玩、年轻的魅力也在于不知所以,但这就有一个问题,把人生想得很戏剧化。过去有一句话叫人生如戏,这是从大的、哲学层面俯瞰,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场游戏一样;但是落到现实生活里面,真的不是戏剧,哪有那样的关系!
陈晓楠 :它是那么琐碎……
老树 :非常琐碎,到了一定岁数才能发现真的是这样。我们看电影,那都是讲故事,真的跟生活没多大关系,人生真的不是故事。
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来找我,说想写点东西。其实他文笔不错,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写。我说你好好写日记。他说应该怎么写呢,我说你每天怎么过就用文字陈述出来。他写了几个星期后发现,都是流水账,特别没意义。我说这就是生活本身的样子。
你一天天怎么经过的都不知道,仿佛觉得自己活在一个传奇当中,活在一个故事当中,当你真的用笔把你每天记下来,你发现你的生活是这么碎片化,这么没意义,这么没有相互的逻辑关联。
你写的过程,是把你的生活凝视了一遍。我们很少有这种用心凝视我们自己。有很多朋友拍照片,我是做摄影研究的,摄影很重要的一点,你平时没注意到的东西是什么样的,你拿着相机对准它的时候,凝视了它,出来一张照片。凝视很重要,凝视了半天得出的结论,就是碎片化的。
所以我一看到《百家姓》就特别喜欢,因为我也在写类似的东西。你所遇到的一个人,一个交集,就会在你的脑子里形成很深的印象。
有次有个放牛的,让我摸他口袋。我一摸,里边一条蛇,我手立马缩回来了。这个人我永远记得他。他把蛇用手一拽,像腰带一样扎自己腰上,这个人太伟大了,就是这么一点事儿,他别的事我也不知道,但是已经足够了,可以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杨葵老师的写作方式,我真的觉得跟年龄有关。这个时候你会在自己的内心容忍或者是认同,或者是喜欢生活,就是这么碎片化的过程,没有那么多的故事性。
陈晓楠 :我今天来这儿其实感触挺深,这一带是我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我从小在科学院这儿长大的,后来上北大附中,离这儿也特别近。原来这儿既没什么科技公司,也不是图书城,是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最繁华的一个商业中心,卖牛仔裤啊什么的。我们这些小孩中午会来这儿买贺卡,这个事那会儿对我们特别重要,送给谁、送什么样的。最喜欢印了一幅日出图的贺卡,觉得好浪漫啊。今天来到这里,好像回到原来时间的那条河里,我走向你们的时候,有一种很虚幻的感觉,走在同一条路上,步伐都是差不多的节奏,你就会想,时间的力量根本不以你的烦燥、惊喜、焦虑……完全不以这些东西为转移,就自己慢慢往前走。就像你说的,在你凝视他的时候,五年十年十五年,一辈子,凝视它,你会发现它的力量。我们能做的就像二位,通过小人物,通过个人内心的凝视,把它记录下来,不仅能让后世的人知道这个时代的人在想什么,而且我觉得,人内心的东西是可以超越很多时代存在的。
我记得老树在微博里介绍杨葵的书,说在这样的一个花里胡哨、乱七八糟的时代,很难得有这么一本从容的书。其实你们二位的作品和这个时代的节奏都不是特别吻合,这个时代真的是花里胡哨,是一个速成的时代,人们需要大起大落。有人就说,这是一个手机屏幕滑动你所有的情绪都带电的时代,是阅读任何作品都不想承受太多痛苦只想赶快消费的时代,你们做的,都相对比较淡,不是浓妆艳抹的东西,我觉得需要相当大的定力。
杨葵 :确实。就像树老师刚才说的,需要“凝视”。我一直在想他说的“凝视”,很有意思。开始只是不自觉的凝视,慢慢地,凝视本身又被自己觉察到。这样反复的次数多了,可能所谓的“定力”就出现了。就是所谓的自觉吧。
陈晓楠 :这要有一定年纪和阅历的操练,得到了老男人的时候才有?
老树 :我说一个感觉,我们写作也好,画画也好,都容易有一种诉求——希望给谁看。我这个人比较懒散,始终这种意识不是很强,唯一意识比较强的就是写日记。写日记是给自己写的吧?恰恰相反,心里永远有一个潜在的读者。你希望你的日记有一天假装忘在哪里,恰巧被他看到了,看到了你本来就是想给他写的话。
但是到了后来,慢慢开始明白一个道理,至少我个人的感觉,这就是你自己的。我这个人,怎么说呢。记得当年咱们看的《红灯记》,鸠山劝李玉和投降,引用了佛家的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当年把这个话都理解错了,这句话极其重要,所谓为己就是有自觉的问题,你活在自己的内心里面,你对自己基本的诚恳非常重要,这不是自私。
要从写作的角度来讲,有一些人一写作就是为了全人类,如果他们没有看到我这个东西这个世界可能就完了,有的是这样的伟大的写作。但是慢慢你就会发现,写作就是自我表达,当你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会从一种形而上的高度来观照自己,最后还是回到自己。当然境界不止是字面上说的这个,会稍微高一些,都是为自己的。
写成一本书或者画成一张画,到了公众面前大家说这个说那个,这个严格意义上说跟我没有关系,每一个人读到的还是自己。我给出一面镜子,每个人在这本书里或者这幅画里照见的也是他自己,我们两个其实也没有关系。
当然有的人会说,通过看这个人的画窥见了他的秘密。不是的,其实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每个人的表达首先是为自己写,我要表达我的经验,我思考的经验,我知识的经验,我日常的经验。当然阅读有有一种企图,老想听一个故事,老想听到“突然”。比如说看韩剧,我看过一些韩剧,长的模样都挺光鲜,但是,我觉得看那个东西欺负自己的智慧。都是讲一个非常严密的故事,里面的逻辑关系那么缜密,可你一看就知道必然要发生什么。生活当中会这样吗?我今天努力了,明天老板给我涨钱?没这么回事,都是偶然事件,生下来就是偶然,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死。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接受这种生活的偶然性,大悲大喜,慢慢变得从容不惊,就这么点事儿。很平常地接受这一切,认真应对过这些,我觉得就可以了。所以我现在特别喜欢平淡的东西。
我喜欢的比如汪曾祺先生,当年读到他的《大绰纪事》那些作品时,汪先生好像还没大红大紫,我就觉得特别好,那时候没有几个人知道。我1983年做毕业论文的时候问导师,汪曾祺是谁?不知道。那时候老师都不知道。后来我联系了一下,我们还见了一面,一见是一老头,吓我一跳,原来是《沙家浜》的作者,沈从文的弟子,跟巴金老婆是同班同学,这么一个老头太厉害了。但是人家讲苦难的时候,就跟讲别人的事一样,那种平淡!老头坐在我对面给我说经历过的那些事,就仿佛那些事与他无关,岁月以及这个人的境界是何等的了得,我非常佩服他。
生活就是平淡构成的,我们对阅读的期待,对于画的期待,包括对自己生活的期待,不要指望什么奇迹。现在都是耸人听闻,“快点看!不看就被删了!”微信上老有这个,你感觉活在一个传奇里。我觉得太扯淡了,太可笑了。
陈晓楠 :一个下了猛药的时代。您刚才说到“诚恳”,我觉得这个词值得聊一下。杨葵你的书里面也谈到所谓“真率”的问题,其实是个特别难的境界,或者说是分寸。你常常不自知是不是真,是不是率。有时候你会下意识地讨好,下意识地抖包袱,或者下意识地抒情,下意识地感动自己。你也多次提起做作的问题,我记得你说你讲的这个不仅仅是写作,更是做人的问题。
我相信很多东西不是从写作本身的技法得来的,可能在你的生活和为人方面有些这方面的经验。你怎么看待所谓的诚恳和真率,无论是活着还是写作?
杨葵 :这问题可以写好多本书。具体到我自己,我喜欢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解决问题。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每个人都容易在脑海里塑造一个别人脑海中的自己,你老觉得,我如果这样,别人就会这么看我;我如果那样,就会那样那样。后来发现,你认为的别人怎么看你,和别人实际怎么看你,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当这个釜底之薪被抽掉,你就会想,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吧。这样一来,就诚恳了。
陈晓楠 :拿我们的行话说,就是去镜头感。其实很多时候这种角色感和镜头感非常害人,但是很多时候是不自知的。常常还不是一个镜头,感觉是群发的,好像一颦一笑,都有观众在看自己,这种镜头感是挺难除掉的。
杨葵 :这还只是第一层面,关注是不是在讨好观众;更深入下去还有向内的一层——是不是在讨好自己。比如说,我就想今天喝喝小酒,把一天混过去,这个时候就有两个声音会出现,一个声音说:人生不能虚度,另一个声音是:就是要潇洒一点。这两个声音到底怎么交战,各自采取哪种战术,以及最后的结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哪来的这种打架?我认为,只要还出现这种打架,就是还没有做到真正的诚恳。当我虚度光阴,从不因此而悔恨;当我积极进取,也不会踌躇满志,这个才是更深一层的诚恳。
陈晓楠 :其实这个类似修行,二变成一。树老师我们所看到的您都是喝点小酒、抽点小烟什么的,是不是其实也一堆烦乱的琐事?真实程度有多大?
老树 :人是个体,但要混在人群之中,所以受社会性的、文化的暗示比较多。很多人有这种纠结,这种矛盾,你受的教育跟你的身体有时候打架,比如此时此刻,我就想躺下,这个天儿真应该躺在家里,这都是纠结。关键是什么呢,我所谓的诚恳,有时候我们在现实当中就要欺人骗人,但是能不能做到不自欺?我觉得很难。在我的理解里,不自欺向内的这一块更重要,是对于自己的大诚恳,基本诚恳。你可以骗别人,不能骗自己。
说一个体现吧,就是对羞耻的态度,人要不面对自己的羞耻,就会变得特别软弱。我当年还是文学青年时候写小说,写的都跟自己没关系,仿佛大家都在做一把椅子,我也做了一把,如此而已。后来我发现不对了,我学的是做椅子的手艺,从来没有跟“我”发生关系。我就特想写一点跟自己发生关系的,捏着鼻子咬着牙,很痛苦,真的极其痛苦,就是脑子里所有的羞耻,自己都不敢面对的东西都写出来了,这个很难。写完以后,发不发表没关系,就感觉一颗石头落下了,老子今天开始可以出门提刀杀人,就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你把自己都放倒了,还能放不倒天下人?这是我经验中的诚恳。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重要,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些黑暗和阴暗的东西,你必须面对它,你不面对它,每天绕着走,最后永远解决不了。所以好多事情躲躲闪闪的,不自信什么的,至少你这一生有这么样几回,做那么几件事情,就突然过去了。我那小说后来被压缩了一半多,现在回头看,从那以后我就感觉,很多问题再也不遮遮掩掩了,可以堂堂正正的就这样干。
人都有自己的隐私,隐秘的东西。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一个人在厕所里的时候特真实,脑子乱想,有时候自言自语,一出来之后人模狗样了。厕所也是一个好机会,当你发现那一刹那的真实,我们能不能在现实当中变成一种常态?非常难。当然现实生活当中也不能老在厕所呆着,就是举个例子,打个比方说这个意思,给自己一个机会,让自己交代自己。
陈晓楠 :而且只有这样,才感觉到一种自由。自由这个词常提,但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财务自由?时间自由?还是什么自由?可能内心对自我的真实是一种真正的大自由?
杨葵 :前两天刚看到句话,说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仔细想这话,不一定全面,但说到比较核心的东西。但是大多数人第一念头想到的自由,都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其实跟“自由”恰巧是相反的。联系到现实生活,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当然这跟经济能力、吃喝拉撒都有关系。但是所谓经济能力这种话,又是各自树立的概念,怎么就叫有经济能力呢?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我这些年见到一些人,也没什么稳定、富裕的经济来源,但是挺自由的。自由和经济能力有关系,但关系没那么大。
陈晓楠 :老树,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让你觉得焦虑的事么?
老树 :焦虑少了。到了一定的地步,过去特别看重的事现在不那么看重了。比如,我平时跟学生就跟哥们一样,他们遇上事儿会来找我,女学生失恋,来哭,我是经过这个阶段了,再看这事儿就很可笑,我一般会跟她们说,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不是有的是嘛!就类似这种话。这是我的真心话,不是应付她,但是她体会不到这个境界。
我刚毕业的时候见了很多老先生,像冯友兰先生,你去问一个问题,就觉得自己这问题很伟大,希望给一个解答。人家给你倒杯水就走了。我很愤怒,我想起这么伟大的问题,你们不给我解答。到了一定的岁数就明白,当时他即使告诉你,你也不可能明白。就是这个道理。所有的存在都是境界性的,只有你到了那个境界,突然觉得原来是这样的。当时说隔着层呢。
所以我就说,人有时候想得太多。想是应该的,更重要的是行,是做。真正的、认认真真的过好每一天。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当然也有境界高的,就靠想就想明白了的,那叫先知者,咱们不是先知。
陈晓楠 :你有很多粉丝,他们觉得你那些诗把他们带入仙境一样,这么多人围观你的人生境界,你会有压力吗?
老树 :没有,我觉得没有多大关系。要不我刚才说岁数呢,多少粉丝了,怎么涨那么多粉丝,我很少注意这问题,我觉得没有意义。
我是个很不喜欢被围观的人,要不我很少参与这种活动呢。我唯一跟公众在一起比较多的时候,就是给学生上课。我现在好多了,可以稳稳当当坐这儿,过去特不喜欢。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讲课,准备了一个星期上讲台,一节课45分钟,讲了15分钟说完了,后面就不知道怎么说了,就问下面同学你们有问题吗,没有问题。这时候我还得讲,没东西讲了。那时候年轻,没有经验,不从容,就紧张。年轻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陈晓楠 :杨葵,《百家姓》是不是还会再写下去?你写作的其它计划有哪些?我印象里你就天天云游,看你的微博都气死了,今天这儿明天那儿,你的生活和你的写作是什么样的关系?
杨葵 :那都是表面现象,苦差事也不少,都闷头做呢。你们看树老师的画,每天跟仙人一样,但他生活中也必定有忙乱时候。
我喜欢一个词叫“随大流”,文气点儿叫随波逐流。该饭局就饭局,要不就别答应,答应了就去,哪怕是个无聊饭局,也别再为这个事儿操心,来回琢磨多累啊。
写作呢,我是个业余写作者,比较运气的是,我写的这些内容,和我个人日常生活结合得挺紧。反正每天也就读读书,玩,写也写的是这些。更何况,写写还能让阅读更深入。
对我来说,基本上阅读、生活、写作三者都卷在一起了,生活即工作,工作即生活。阿弥陀佛!

转载请在文章开头和结尾显眼处标注:作者、出处和链接。不按规范转载侵权必究。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授权事宜请联系作者本人,侵权必究。
本文禁止转载,侵权必究。
授权事宜请至数英微信公众号(ID: digitaling) 后台授权,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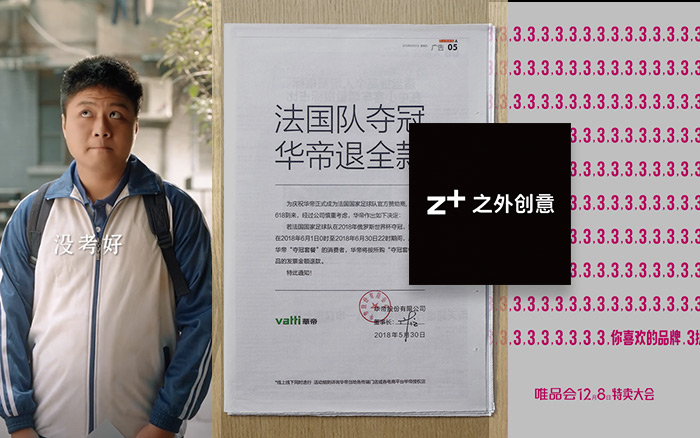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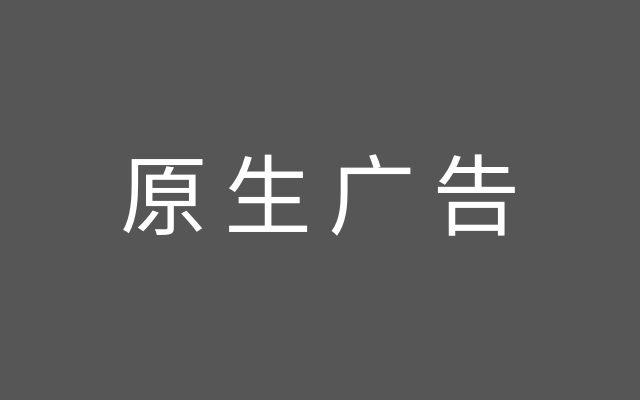



评论
评论
推荐评论
暂无评论哦,快来评论一下吧!
全部评论(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