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好奇心日报
作者:王珊珊
“大家都是在舒适区里边不断地往里叠加。但是在舒适区里边不舒适的人在哪儿,他们会要求什么样的东西才会感觉舒适?”
《见字如面》去年 12 月底刚在黑龙江卫视播出时,收视成绩毫不起眼。但是随着张国立、归亚蕾等念信的片段在网上传播,这档综艺随即在过年前后赢得了好口碑。
喜欢它的观众们发明了一个词,“清流综艺”。另一档过年期间收视率第一的央视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也被归于此列。观众们联想到了《舌尖上的中国》和《我在故宫修文物》这样的纪录片。因为念信、背诗主题带有人文色彩,而在国内以真人秀、喜剧为主的综艺节目中显得别具一格。
不过事实上《见字如面》并非原创。英国原版《Letters Live》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在 2013 年发起,每年邀请来自音乐、影视、艺术、文学等领域的名人到剧场内现场朗读那些“理应受到更广泛关注”的书信。中国观众知道它,大多是因为“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
英国原版《Letters Live》

相对于《Letters Live》,《见字如面》是更加直接的娱乐产品。节目组用将近一年时间,选择了从古至今近 90 封私人信件,花一个月录制,由明星现场朗读。节目的舞台背景非常简单,只有一个讲台。
在《见字如面》的导演关正文看来,“对认知价值的需求”一直是一种常识,在今天品种单一的国内娱乐市场中,甚至会显得更加强烈。
关正文的公司“实力文化”前几年还制作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那两档节目的形式都是中学生比赛,更加固化、应试,没有引发更多观众的讨论。但是它们都获得了商业上的回报。
在接受《好奇心日报》的采访中,关正文说自己“不是一个纯商人,也不是一个纯文化人” —— 这句话的确符合他的工作经历:他是 1960 年生人,曾经写过小说、写过诗,做过《民族文学》杂志社副社长,从 90 年代起进入电视圈,做过访谈、纪录片、春晚设计等各种工作。
《见字如面》导演 关正文

看到这样的履历之后,你可能也就不奇怪他为何会在综艺行业中专攻此类节目。他一方面描绘“多元化”的合理性,一方面将“感官娱乐”的盛行归于暂时的荒诞。
这位 57 岁的制作人回答时语速果断。不过他在面对一些问题时候保持着警惕的距离,例如当我们在采访开场,说想来谈一谈节目背后的文化、社会现象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这很敏感”。
Q:你觉得节目能火是因为太厉害,还是因为太稀缺?
G:首先我觉得它的火是因为它回到了常识,就因为这种认知价值的需求是带有普遍意义的,非常强烈,非常巨大,而且非常恒久。人们一直需要这个东西,但是当我们的精神消费品和我们的文化或者娱乐产品里边,这些东西含量少了的时候,实际上这个需求反倒被郁积,变得更强烈。
感官层级的娱乐,实际上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是主流的,就是它存在,而且它有必要性,它是多元生态之一,那么会有一个层级的人会去倾向于消费那些东西,即使你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你也可能会有那种说我今天就是不想动脑子,然后你就是想被逗乐,那么这个消费也是必然的,也是应该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
但是你知道更大的快乐或者说即使从娱乐角度来讲,更大的快乐其实来自于你的思考的快乐,你能够感受那种叫人类文化中微妙之处的乐趣,还有那种比如发现的乐趣等等,那些乐趣所给你带来的消费的快感,其实远远大于感官层级的娱乐。

Q:感官层级娱乐并不是主流?
G:对,是支流,它不是主流。或者说你能在大数据里面看到它占比可能很大,但是它是阶段性占比,因为全世界你比如说,我们知道有很多民族现在每年图书的阅读量都很大对吧?像什么日本人每年读 40 几本书,什么以色列人读 50 几本,匈牙利人读 60 几本,我们自己一本不到。那些人为什么在一直读书?其实他们那种精神消费是特别稳定的一个状态,他没变。
我们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感官型娱乐在前几十年可能有点稀缺,就是那品种太少了,于是集中的有一个释放。但是你不管是怎么样,你放在历史的阶段里边去看,你集中释放的时候,你的占比很大,但是你放在长时间历史看,它不可能永远占那么大比。
因为它满足不了人们的这种真正的精神生活的需求,甚至满足不了娱乐需求,因为你老咯吱人,这玩意儿谁也受不了对吧?人自己在整个思考过程中所享有的那种最大的快乐,那种游刃于智慧之间的那样的一种巨大的快乐,那是任何感官型娱乐根本没有办法替代的。就好像没有爱情的性跟爱情(的性)之间的差别是一样的对吧?
Q:但是就像你说的,现在我们自己平均一人可能一年读一本。
G:但是你知道对叙事类作品的消费,比如说你是看书只看了一本,但是你拉片你看电影,或者是看电视剧你可能看了好多,看那些东西同样也是为了认知社会,而不仅仅是感官型消费。
长期停滞于感官型消费,人会不满足的。所以好戏还是会轰动的,你比如说电影头两年有所谓的票房喷发,但是都是一些笑闹剧,一些感官戏。你到 2016 的时候,你再用感官戏试试,票房不认了。
Q:为什么思考的快乐会成为稀缺品?
G:首先就是应试教育确实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一直说我们应该多读书,但是应试教育本身并不能被翻译成读书,它可能是上学,上学在过去跟读书是一个意思,现在上学跟读书可能不是一个意思。因为上学有可能你是在读考卷,你是在为了那张考卷来不断地积累你的应考能力。
但是读书的乐趣是另外的,读书的乐趣在于你去认知你的社会、你的身边的事情、过去的事情,你的身边的人和你自己等等,这些东西是读书的最核心的目的,不管你读的是人文还是科学的对吧?都是为了认知这个世界。那么这样的一个认知必然要经历某种独立思考的过程,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人之为人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今天这种思考能力的缺失或者说思考习惯的缺失,实际上是我们特别大的一个遗憾。它最终会阻碍了个人的发展,最终会阻碍了我们整个民族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力。
Q:一开始你们是否担心会和网络综艺脱节?
G:我跟腾讯曾经说过这件事情,他们就说在一定程度上说所谓的网络视频节目类消费是文化层次不高的,是怎么怎么样,娱乐追求明确的等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我说实际上我们现在对大数据的感觉或者是使用,实际上是初级阶段的,我们没有办法辩证在你那个所谓大数据里边,就是所确定的视频节目内容制作的舒适区,那个舒适区里边有多少不舒适的人,因为你没有那个品种去测试,你品种没有丰富到那个程度,大家都是在舒适区里边不断地往里叠加。但是在舒适区里边的不舒适的人在哪儿,他们会要求什么样的东西才会感觉舒适?
Q:为什么要用朗诵的形式?
G:我们特别地排斥朗诵(这个词)。
Q:这个词有什么问题?
G:就是因为其实没有这么一个词,就是你知道朗诵是我们汉语被异化了的一种表达状态,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朗诵是那种抑扬顿挫式的,包括比如说诗朗诵是吧?红日、白雪、蓝天,就那种特别慷慨激昂,它是非人性化的,是非日常化的一种异化的一种特定的艺术表现手段。但是它往往也跟着那种叫装腔作势,跟某种的这种假也有某种关联。我们甚至都不愿意叫我们叫朗读,因为你知道我们朗朗的书声从小学一直到中学,上来接触一篇新课文的时候,都说我们集体朗读一下吧,谁谁个人朗读一下吧。那个朗读本身都不是我们人在说话对吧?
那所以我们其实比较警惕。我们实际上用一句话去说,比如说我们提倡的是角色化的演绎,是人物化的演绎,是生活化的演绎,是谁谁谁演绎了这封信。
每一封信都是一台大戏,但是它是真实的,是由真实人物上演的。它的微妙、它的冲突、它的那种跌宕起伏,是特别漂亮的。
Q:许子东会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姿态来解读信件,评价社会现象和人物。这个是你们希望他承担的功能吗,不要主旋律教导风?
G:实际上许子东的作用是激发思考,而不是替代思考。为什么我说他实际上代表的是主流,就是因为他的思考方式是人类在面对这样的素材的时候,本来就该有的方式。然后人去读这一封信的时候,本来就应该读到它应有的厚度,而不是把它读得扁平化。
我们的电视大部分的功能,就包括我们主持人其实一开始也有不适应,就是因为就是她总是用一些特别正确而简单的结论去概括,去完成所有的什么所谓引导什么之类的。后来我们主持人进步也很大,也很不容易,我们在现场一直在交流,就是你一定要看到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复杂性。
就比如说一个太操蛋的事了,这事我简直义愤填膺,比如说我们选了徐志摩跟陆小曼之间的往来信。实际上人类爱情是人的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经历,人类的爱情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理想化的。
Q:你对“主旋律”和“正能量”这两个词怎么看?
G:我觉得是这样的,我比较喜欢主流这个词。然后这些主流是相对于比如说感官曾经娱乐,尤其在今天它变得有效的。就是因为人类文化一直是什么样的,它不因为互联网的兴起而产生多么重大的变化。
比如说你在全世界范围里面,你没有看到兴起了什么所谓网络文学,或者是网剧或者是网综,只在中国能看见,明白这个意思吗?
Q:“网”在中国特别被拎出来的意思?
G:这个拎出来往往是投资人拎出来的,市场或者是商业化运作的人,资本运作的人拎出来的。
Q:但是美国的 Netflix 是最早做网剧的。
G:你知道你能看到《权力的游戏》,它是 HBO 剧,在中国是腾讯系,是网剧。你能看见《纸牌屋》在美国是互联网传播的,在中国也是互联网传播的。但是你能说《纸牌屋》不是好电视剧吗?或者它放在任何传统媒体上有问题吗?没有。
在那些文化生活正常的环境里面,好戏就是好戏,坏戏是坏戏,不管它通过网络传播,还是通过传统媒体的渠道传播,渠道只是渠道。你通过网店卖的手机,跟你通过门店卖的手机,这个手机凭什么要有区别呢?所以这是一个伪概念,在中国是一个短暂的有效概念。
Q:网上的东西能够更迎合年轻观众?
G:跟年轻人没有关系。比如说大众也需要一些浅层的娱乐,但是过去我们的传统媒体可能供应的不是特别的充分,那么我们品种的丰富性可能也不够,活跃度可能也不够。喜感可能因为互联网的宽松,可能会被更多释放。但是释放完了呢?又怎么样呢?你还能上哪去呢?然后你会发现,其实人类文化生活最终还是会回到它的相对稳定的主流的状态下。
Q:“相对稳定的主流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
G:人类文化实际上这么几千年形成下来以后,有它自己一定的规律,有它自己的一直在传承的价值观。比如说什么是好书,什么是好的文学,什么东西是经典,甚至什么是好歌,都有一定的规律。
所以你要说《小苹果》是好歌,这事你放不到历史上去,对吧?小苹果是感官娱乐的,它是口水的,但是你得承认这确实是一个大众文化现象,所以它有短暂的爆发。但是无论如何如果它要是能够成为什么百年金曲,这事就有一点荒诞,或者最起码今天我们想来会感觉荒诞的。
但是你知道我们今天推崇的不管是贝多芬还是莫扎特,当时在他自己的国家不管在德国也好,还是在奥地利也好它是有相当的流行性。我们过去古代诗歌写作的时候,都是为了传唱的。传唱实际上也是为流行,不是因为它是小众窄众的,或者是被少数文人所推崇的,于是它变成经典。实际上它天然过去也具有大众性,人类文化一直有这样的大众主流。
那时候大众主流所达到的精度,所表现的人类情感的丰富性,给每一个人所体规的认知价值,实际上那个东西是恒定的。要不然我们读书干吗啊?我们撑的。
Q:节目开场说了一句“用书信打开历史”,这是你们想让观众看完的感受?
G:对,非常明确的一个感受。因为我觉得《见字如面》跟怀念书信传统的关系不是那么大,或者说不能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对即将失去传统的某种抚摸,它的最核心的功能是给人们提供对过去历史的认知价值,同时提供对于人性、对于人际关系的可能性、社会关系的可能性,那这样的一种认知价值,这是核心。
过去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更多的实际上它是一个他人的概念,是一个他者的概念。有点像我们人类对于叙事类作品,实际上一直具有特别永恒的需求。
那么这个需求的核心动力,是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直接的生命体验之外,去更多地经历他人的人生。这样的一个经历会带给你对于你未来的生活、你下一秒的生活、你的遭遇带来一种处置上的准备。那么实际上每个人都需要这个东西,一个人的一生活得是不是精彩,他对世界的了解程度,对他人和自己的了解程度,决定了生命质量。所以认知历史实际上是为了今天的人,是为了今天人面对以后,认知他人、认知我们自己、认知人的情感、人的关系的可能性,都是为了丰富自己。
Q:有什么内容是敏感的?
所有的历史都应该是被正视的,甚至应该被尊重的,因为它给我们的今天都带来了启发和借鉴作用。所以只要你的历史观正确,没有什么历史是不可触碰的。
Q:正确是从什么立场出发?
G:我不知道,应该是知识分子概念,就是你对于历史,实际上就是它是一个作用于明天的事,不是一个你在历史那纠结什么恩怨的事。

Q:你怎么看这个时代,人和人之间交流方式的变化?
G:这么看,首先就是我们今天的交流,实际上比过去多的多。包括我们信件的产量,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往来,是比过去多很多的时代,比如写信和等信,我小时候一封平信还得一个多星期才到达手里面。既使是本市的信也得几天,你才能收到一封回信。
那时候的交流,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说,那时候具有美感,因为你老期待。你写了一个求爱信,然后 7 天之后你才能收到回信,今天说那个发一个信息,你 3 秒钟不回恨不得就急了。
那好,首先是说人类的交流状态是前所未有的,非常多。很多人会指出来说,我们今天的语言就是表达能力在退化,是扁平的,是有很多替代品的。比如说我们在《成语大会》里面,蒋方舟就曾经讲过例子,就是什么都叫醉了,无奈也是醉了,这个陶醉也是醉了,生气也是醉了,反正什么都是醉了。但是在我看来,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语言汉语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活泼的状态。
Q:你觉得这种状态是好的?
G:它肯定是双面的,就是一方面有它扁平化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它生命力重新激活的问题。你看这两年我们新增了多少词汇是过去几十年没有过的,在国家语委反复管控的时代,实际上语言是僵死的。而今天的语言是充满着活力的,是重新焕发了汉语生命的,而且很多词汇的表意功能,实际上被重新注入了我们今天的生命的。
包括我们把表情发明成世界性语言,这样不同的民族之间不同的语系之间,实际上大家交流的过程中,实际上大家伙用到的东西,也都挺有意思的。
Q:但是“活泼”的另一种结果,可能是价值观混乱,或者浮躁?
G:乱,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正向把它翻译成多元。多元跟浮躁是两回事。浮躁指的是没有厚度,飘在表面。那么实际上任何一个时代,对于最广大的大众来讲,你都没有办法要求它的深度,就是精英永远是少部分的人。而在我们整个国民教育的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实际上在我看来,精英群体是在非常快速和大数量级地扩大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有独立思考和感知能力,而不是越来越少,这个比过去的时代是进步的。
当然我们的应试教育,给我们整个教育成果带来的局限性,也还是非常带有伤害性的,就是还有太多的人,实际上不会自己读书,不会自己学习,不会自己思考,还有太多的人,只会等待喂养和吐出来标准化产品。就是反正就是,我要学一样东西我就上个班,然后被人考一次然后我拿一个证书,这事我就解决了。但是实际上这跟生活不是一回事,这跟你个人的发展也不是一回事。
Q:你说的比较乐观。你觉得你是一个不太喜欢批评的人吗?从知识分子的立场说。
G:我觉得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基本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态度。当然你可以有个人的好恶,但是首先你应该看到就是多元化的、多样性的生态是一个健康的生态,任何时候如果就是完全单一,就是完全摒弃多样性,那实际单一品种的发展可能也会受到摧残的。它也不会健康发展的,哪怕你是唯一被允许鼓励的。
我们曾经经历过所谓八个样板戏的阶段,全国一共才有 8 台戏。那你说它火透了,但是那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生态。
Q:你为什么要从出版界跳到电视娱乐界?后者有什么更吸引你的地方?
G:在我看来出版也是娱乐界。在我看来娱乐是一个大的概念,就是任何能够带来快乐的。所以出版也是娱乐,电视也是。只不过在我从出版转电视的那个时候,正好是出版界刚刚开始衰微的时代,然后是电视的影响日益扩大的时代。谁都有可能,更愿意去做那种影响更大一点的事情。
当然也有对个人能力判断的局限。因为我是做文学出版的,我肯定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但是当时因为我作为责任编辑,比如说我编过贾平凹的,编过莫言的,编过什么刘震云的,编过什么阿来的,编过王朔等等的。
我见到太多的精彩的作家,然后我觉得我不是。我觉得我不是。你从二三十年之后,你现在再看他们,他们真的还是特别的棒。一个时代有他们,就是你可以做一点边缘的事吧。你就别在那条道上挤了。
Q:你有没有什么不敢尝试的,或者没有做出来的?
G:首先我没有什么不敢尝试的,然后我们也不断地会出新的东西。因为其实每次出新的东西,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快乐,当然也是一个巨大的痛苦,因为每次都会脱几层皮,然后压力巨大。
它的最大的挑战实际上在于,其实每次你都试图超越常人的经验,而你超越常人经验之后你会发现,你进入一个别人无法辨认的地带,包括《见字如面》都是这样的,你跟他讲卷福(《Letters live》节目),你跟他讲英国什么人出一本书什么的都没有用,可能今天讲是有用的。但是在当初讲,所有人都认定了,你就是一个小众的东西,你不可能走多远,你不会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和市场价值。然后你最终把它实现的时候,这个快乐是巨大的,但是那个实现的过程本身压力是巨大的,就是我们不是输不起,但是你肯定不愿意输。
Q:你在电视行业这 20 年,你感觉变化最大的是?
G:首先我觉得我们自身的成长,成熟这是一个变化很大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离不开外在的大环境,比如说电视节目的产业化可能,市场化的发展。实际上我们在内容创新上,空间就大多了。这跟过去行政体制管理下的创新,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过去你要在台里面,你要想做一个新节目,你得层层报,然后一层层批下来然后领导有一层层的指示。这个时候实际上更多执行的是领导的创新,不是说不好,但是确实更多执行的是领导的创新,除非你是一个头。
但是我们现在在相当程度上,是独立的、自主的创新。我们创意一个节目,我们把它做出来,电视台一样可以,你要咱们就合作,你不要就算了,就是这样的。
图片来自节目海报和剧照
- END -
关于「好奇心日报」:
qdaily.com — 把世界变成问号。每日报道与你有关的商业新闻,无论它是科技、设计、营销、娱乐还是生活方式。另外还有一个“生活研究所”供你吐槽生活。
转载请在文章开头和结尾显眼处标注:作者、出处和链接。不按规范转载侵权必究。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授权事宜请联系作者本人,侵权必究。
本文禁止转载,侵权必究。
授权事宜请至数英微信公众号(ID: digitaling) 后台授权,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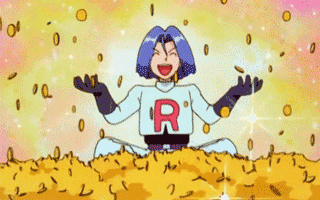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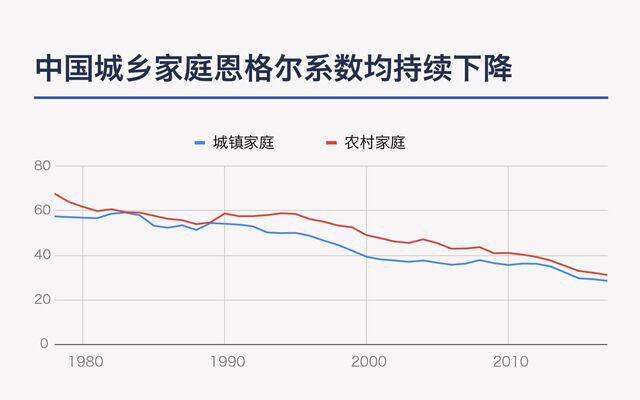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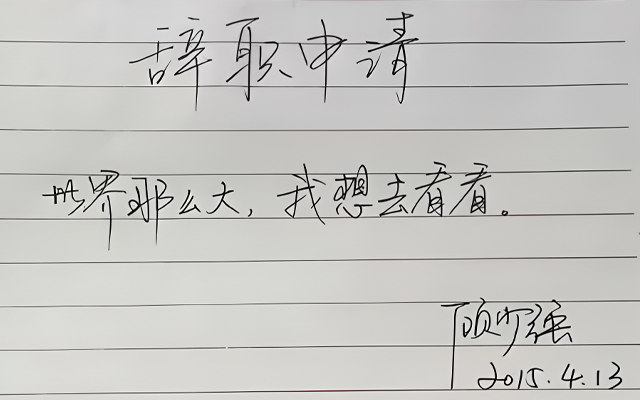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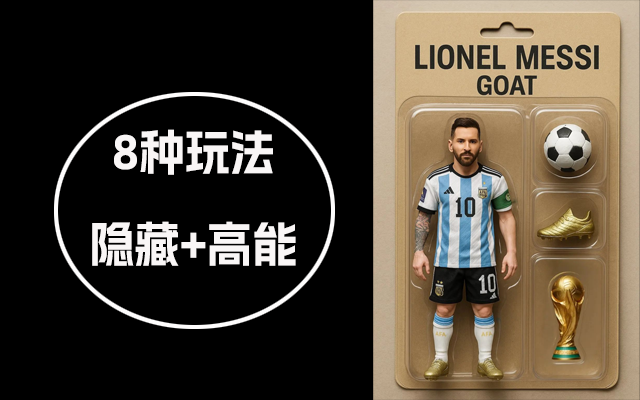





评论
评论
推荐评论
全部评论(3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