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100万日本人:逃避虽可耻但有用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7年:“让压力见鬼去吧…我就是失败…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来源:看客insight(pic163)
摄影:Maika Elan、综合:赵昕萌
撰文:曹雁南、编辑:简晓君
在日本,一切都具有两面性。它既现代又传统,看似纷繁热闹,却也相当寂寞。
餐馆和酒吧总是人满为患,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大部分顾客都在独自用餐;不论任何时候,从山手线到中央本线,都能看到疲惫不堪的白领。
和这些置身于人潮、拼命活着的社会人不同,在无数个霓虹灯照不到的地方,有一群“失踪人口”,他们从拥挤的社会生活中悄然撤出,终日闭门不出,以一种近乎诡异的方式“调节着日本的平衡”。
他们的生活被封装在这样的房间里。

“失踪了的100万人口”
佐藤,22岁。
睡眠时间:一天16小时。
朋友数:0。
不上学,不工作,没有固定收入。家里蹲4年,对半径3米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一天也不曾离开过六张塌塌米大小的单间公寓。
——以上是《欢迎加入日本废柴协会!》的主角设定。说起来有点荒诞,这是一部没有任何魔幻色彩的,仅仅是在叙述的现实剧。
在日本生活的半年期间,越南摄影师 Maika Elan 见到了不少活生生的“佐藤”,他们被称为 Hikikomori,蛰居族。
Shoku Uibori,蛰居7年。

43岁的 Shoku Uibori 就是“失踪人口”的一员。Maika Elan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7年。偶尔,他会在深夜出门,前往 7-11 购买泡面和啤酒。
他曾是一名商人,拥有过自己的公司。破产后,他整日把自己锁在屋中读书。10平米的房间就像一个当代孤独实验室,尘世的气味被隔绝在外。在这里,一切软弱和不健全都因缺乏参照物而变得无可指摘。
“就像仓鼠爱它的笼子,没有笼子,仓鼠会不知所措。”
Shoku Uibori的房间

Shoku Uibori 并不孤单。像他这样的蛰居族,日本大概有100万。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定义,“蛰居族”有着共同的特征:拒绝参与社会生活,特别是上学或工作;没有任何亲密的社会关系,“失踪”时间超过6个月。
而最高记录者,蛰居时间长达40年。
《蛰居族》双月刊报道了蛰居现象
其中提到34%的人蛰居超过7年

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15到39岁之间的蛰居人数达到54.1万人,其中80%是男性,且大多数人拥有硕士学历。
而研究人员则认为,真实的数字远远不止于此。
由于这项调查把40岁以上的人排除在外,蛰居族们又有自我隐藏的特性,九州大学教授、神经精神病学家加藤孝宏推测,目前至少有100万日本人处于“隐居”状态,约占总人口的1%。

Fuminori Akoa,29岁,蛰居一年。Fuminori Akoa的自我评价很高,觉得自己大有一番作为,但兴趣和目标又总是变化无常。如今他已经渐渐迷失了方向。
“逃避虽可耻但有用”
一百万人“消失”了,不社交,不工作,长达数年渺无音信。
情况稍微好一点的,会趁夜晚没人的时候出去溜达一圈,比较严重的,则拒绝走出房门,年迈的父母只能通过食物包装袋来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

Riki的房间被贝壳面、零食和散落的杂物堆满。有时,他甚至不需要吃喝,因为心理的障碍比生理的需求大得多。
“其实他们身体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有意识地把自己封闭在家里,每天就是看书、上网、玩游戏。”加藤博士称。
蛰居者喜久井田在《我为什么不停地玩电子游戏》的网络日志中写道:“从7岁开始,我不再上学。洗脸,换衣服,吃饭,做完这几件事,上班族出门上班,学生出门上课,我开始我的游戏。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内心的压力大到足够杀死一只恐龙,但有游戏可玩,我不至于疯掉或者自杀。”

对桥本雅来说,父母的期待是一件沉重的事。他曾经是班里的佼佼者,某次考试失利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退学后,他成了蛰居族。

他曾寄望环球旅行会使一切有所不同,但实际情况是旅行结束后,桥本雅继续过着蛰居生活,且一呆就是七年。
这些人里,有的是遭遇校园暴力后不愿意去上学的孩子;有些则是成年人,因为失业或者求职失败,回到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勇气出去。
除此之外,父母离异、考试失利、感情创伤,都有可能让他们产生“劣等感”,进而陷入一种“未战先忧败”的死循环之中——“逃避”,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抚慰这种情绪最简单直接的方式。
毕竟,逃避虽可耻,但有用。
“我也知道这是不正常的,但我不想改变。这里(房间)感觉很安全。”

30岁的日美混血儿 Riki Cook 蛰居三年。他的家人都在夏威夷,而他独自隐居日本。在他成为蛰居族之前,生活中的小事足以让他感到疲惫,无论是忘记带书,还是找不到新教室。

而事实上,Riki Cook总想出人头地,却又害怕犯任何错误。他认为,一个小小的错误就会导致自己被淘汰,而不去尝试就能避免一切错误——这让他的生活陷入僵局。
“薪资冻涨、未来不明,我们向下沉沦”
“通常来说,这些人的适应力比普通人差,一旦发生某种‘突变’,他们往往会觉得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加藤博士说。
而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学者安迪·弗隆,则把日本的“蛰居族”现象与日本经济的兴衰联系起来。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高度经济增长期”,日本社会就出现了大范围的“不登校”现象。
及至昭和与平成年号交接的历史时刻,空前繁荣的泡沫经济迎来了破灭。与此同时,1990年,青少年蛰居问题首次见诸报端。
2000年前后,由蛰居者实施的恶性犯罪案件接连发生,一名隐蔽了10年的青年杀死了父母,才终于让这个群体彻底浮出水面。
Chujo,24岁,蛰居两年。

当然,这并非日本社会所独有的现象。自从“双失(失学失业)青年”于2004年在香港被发现之后,在台湾、美国、英国和韩国等地也相继发现“蛰居族”的存在。
有研究者称,所有发达社会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经济衰退严重、失业率高的地区更是如此。
但不同的是,日本年轻人遭遇了其他发达国家年轻人不曾经历过的、旷日持久的经济停滞。在安迪·弗隆看来,泡沫经济的破灭切断了“高分数-好大学-好工作”的“传送带”,日本年轻人失去了父辈所拥有的“终身制”工作,转而迎来打短工、打零工的短期就业局面。

Sumito Yokoyama,43岁,1996年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截至2016年,Sumito Yokoyama已蛰居了三年。
经济遭遇重创的同时,原有的价值观也受到极大冲击。
如今的日本年轻一代远离了父辈所信奉的一切。泡沫时代积累下来的物质基础,不仅赋予了他们对自由和享乐的想象,同时也带来了垮塌的可能——对于他们而言,像父辈一样努力学习、认真工作“简直是对生命的浪费”。
就如村上龙在谈到《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时说的那样:“很多人想活得我行我素,选择非正统的工作,或者不按社会规则行事。”
但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只会让生活变得更艰难——在日本社会,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仍然是某种铁律般的生存法则,即使它令人倍感压力。而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人,只能带着耻辱感活着。

Chujo,24岁,蛰居两年。Chujo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但父亲不看好他的选择,父亲有自己的生意,并希望Chujo做一样的事。

在家人的要求下,Chujo曾在家族企业上过一年班,但因压力过大而饱受胃痛折磨。Chujo有一个令他羡慕的弟弟,因为弟弟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当他表现出沮丧的情绪时,家人会变本加厉地训斥他,这更加加重了他的耻辱感。

工作两年后,Chujo开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世界不会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而变得更好”,蛰居者认为,与其面对疲软无望的未来,不如另辟蹊径。
“逃跑,只有逃跑的时候,我才是我自己。”
Fuminori Akao,29岁,蛰居一年。

调查还显示,“男逃兵”的数量要远高于“女逃兵”,在日本,男性往往从初中起就感受到压力,因为将来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两三年的表现。
另一方面,大多数蛰居族来自相对优渥的中产家庭,他们通常被寄予更高的期望。
“在西方社会,如果一个人窝在家里,他们会被告知要出门。”加藤博士说:“但是,很多时候,日本父母无法狠心切断孩子的经济来源,尽管经济不景气,仍然无限期地赡养他们。”

Kazuo Okada,48岁,他曾是一名公司职员。辞职后蛰居在家7年,他喜欢看书和演奏爵士音乐。
不光是年轻人,近年来,40岁以上的蛰居人数正在增加,而这往往是从被裁员开始的。
在没有收入来源的情况下,生活会变得异常艰难。因此,很多年纪较大又没有父母依靠的蛰居族会在“隐退”之前,上班一段时间来积累生存资本。
与世隔绝的时间越长,蛰居族就越难走出家门。
22岁那年成了蛰居男的Yoshiko,起初还会出门买东西,后来网购的普及,打消了他出门的唯一念头。他现在已经55岁,不再出门。
逃避到极限,就无限趋于死亡,连走路、吃饭、呼吸都困难。

蛰居族Sumito Yokoyama躺在他的房间里。这张照片拍摄于2016年,当时他告诉摄影师,他的健康状况不佳,虽然没有严重的疾病,但经常感到疲惫,只想呆在家里。

在这张照片拍摄后的2017年,Sumito Yokoyama在自己的公寓里死去。两个月后他的遗体才被家人发现。
“被需要的感觉,是我努力的动力”
一些本该以天下为己任的“青年志士”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铩羽而归,隐世而居。这令安倍晋三的政府深感不安。
对于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来说,萎缩的一代,既是经济的危机,也是社会的隐患。
2015年,日本千叶市设立第一所“虚拟高中”。次年年末,首相安倍晋三宣布设立心理咨询中心,以专人登门拜访的方式促进这个国家萎靡的劳动力。
Oguri Ayako是Maika Elan认识的第一位“租赁姐妹”,她来自社工组织“新起点”,专门负责与蛰居者定期写信、联系。

Ikuo Nakamura,36岁,在摄影师拍摄这张照片时,他已蛰居7年。大学期间,Ikuo Nakamura的人际交往并不顺遂,逐渐地,他觉得生活里有太多的不公,渐渐失去了与人交往的信心。
“‘蛰居’是一种与社会解除联结的状态。不要心急,你可以一次一次地系上小结。”
2016年8月,时年36岁,已有7年“隐居”史的 Ikuo Nakamura 见到了第一次来家里探访的“租赁姐妹” Oguri Ayako。几个月过去,慢慢地,在对方的帮助下,Ikuo Nakamura开始逐渐恢复。
最近,摄影师Elan得知,两人在那之后便坠入了爱河,且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而Ikuo Nakamura 也尝试着成为一名“租赁兄弟”,以期帮助更多的蛰居族打开心扉。

2016年8月,“租赁姐妹” Oguri Ayako 正与 Ikuo Nakamura 聊天。彼时 Oguri Ayako 拜访他已有些时日。
事实上,这项工作并不轻松。蛰居者从“杳无音信”到“开始回信”,有时需要几个月乃至十几个月的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Oguri Ayako 少不了对着门自说自话,诉说自己的兴趣与爱好,而换来的往往是一段死寂般的沉默。

Oguri Ayako在给另一名蛰居者 Masahiro Koyama写信。

Oguri Ayako 试图与 Masahiro Koyama 沟通。通常情况下,一个社工需要花一到两年的时候带领一位蛰居者“走出房间”。

40岁的Masahiro Koyama已经在自己的房间里呆了10年。这是Ayako第三次到他家来,但他还是没有打开房门的迹象。由于他拒绝进行交谈,Oguri Ayako 只好把信从门缝里塞进去(事实上,很多人从不阅读信件,收到后会直接丢掉)。
当蛰居族们开始慢慢习惯“租赁姐妹”的存在后,他们首先会以回信的方式打开自己,渐而过渡到电话聊天、打开房门,甚至是一起外出看电影。
而最终目的,则指向“职业技能培训”,好让蛰居族们开始新的生活。

除了他们的“租赁姐妹/兄弟”,很多蛰居族拒绝与任何人沟通。

在长达10年的工作生涯里,Oguri Ayako帮助了近五十位蛰居人士成功重返社会。

每周六,“新起点”都会举办餐会。在餐会上,蛰居族可以相互认识,也可以和社工及社工的孩子们互动。

在餐会之余,“新起点”会把一些基本技能传授给蛰居者,包括烹饪,打扫卫生,与他人交谈。
“我在Twitter上遇到的一位女性,她希望我为她拍照,这件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曾经的蛰居族木村说。“当你觉得你是被需要的,你就想要付出努力,特别是当对方是异性的时候。”
除了木村之外,Elan 还跟随 Oguri Ayako 拜访了11名蛰居族。在接触这个群体之前,Elan 承认,起初她认为这些人既懒惰又自私,不过是“日本经济萎靡不振的寄生虫”。
但随着她对蛰居族的了解越发深入,她看到了他们的细腻和敏锐,也有了更多的发现。

蛰居族 Kazuo Okada 非常善于学习,记忆力惊人,且非常善于引用数据。每次煮饭时,Kazuo都会精确地掌握米的重量,保证不多不少250克。
“他们在思想上备受折磨,为自己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工作而感到痛苦。他们想去外面的世界,想结交朋友和情人。”
至于自己的摄影项目,Elan最想拍到的是蛰居族在“租赁姐妹”的带领下,踏出房门的那一刻。

“我不知道那一刻是否会非常戏剧化,还是平静如常。只是,在漫长的禁闭后,他们打开门,迈出去,呼吸新鲜空气,感受被阳光照射的那个时刻,难道不值得记录吗?
外面的世界,其实很值得一看呢。”
参考文章
[1]It felt safe here,Witness,Maika Elan
[2]A psychological ailment called 'hikikomori' is imprisoning 500,000 Japanese people in their homes — and it's more of a threat than ever,Alexandra Ma
[3]Pictures Reveal the Isolated Lives of Japan’s Social Recluses,Laurence Butet-Roch
[4]Japan’s extreme recluses are coming together to create a newspaper for social outcasts,Isabella Steger
[5]《隐蔽青年:症候群及其援助路径的探索》,杨锃
[6]《日本青少年蛰居问题分析》,师艳荣
转载请在文章开头和结尾显眼处标注:作者、出处和链接。不按规范转载侵权必究。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授权事宜请联系作者本人,侵权必究。
本文禁止转载,侵权必究。
授权事宜请至数英微信公众号(ID: digitaling) 后台授权,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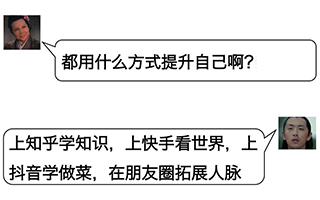





评论
评论
推荐评论
全部评论(5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