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珺,来源:财经杂志 那么多的钱和那么多人的青春烧掉了,留下一个好故事。
(许多城市出现了海量小黄车的堆积点。图/视觉中国)
三年,ofo搬过四次家。办公室迁移恰如其分刻画了这家公司的浮沉轨迹。前三次,由于资金池充盈和团队壮大,办公环境愈见开阔、华丽。只有最后一次是倒退。2018年11月5日,ofo搬离见证它鼎盛期的中关村理想国际大厦。这是幻梦结束的一刻。
一位ofo的80后中层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他原先觉得ofo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很美好,后来他的想法改变了。创始人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赢得战争”,但是“你是那个我们吗?你是那个代价”。
短短三年时间,在资本的助推下,ofo以无可复制的速度攀上巅峰,而又以始料未及的速度跌落。于商业社会而言,这是一个无比极端的案例——所有急剧的内外冲突,在最短的时间,降临在一位27岁CEO身上。
在这个ofo乃至共享单车行业的冬季,《财经》找到15位ofo员工,希望从他们的视角还原这段往事。为了追求故事的完整和中立,这15名员工来自ofo各个分支,加入时间和圈层各异。他们有刚毕业就跟随戴威创业的元老级员工,有已过而立、背景光鲜的中高层职业经理人,也有骤然空降和神秘撤退的“滴滴系”。
它或许是一个令人难以喘息的故事。在大起大落的剧情脚本中,你能看到不同剧中人的剪影。
一个自称在工作中软弱、不与人争的90后,后期看到公司每况愈下,在一次会议上公然对其他部门领导说:“你们太不负责任。” 一名早期加入、后因多轮人事更替离开一线的员工说,他们一直在等。“都到这种时候了,没有人比我们更忠诚,公司危难的时候该我们上了吧。”他说,“结果也没有。到后面,说实话心有点凉。”
一位离职高管发现戴威也变了。在经历大风大浪商业的血洗之后,这个喜欢吃马路对面便利店盒饭和包子、对财富没有贪欲、个性单纯甚至有些内敛的CEO,从去年什么都相信,变成今年什么都不信。
ofo的故事还未剧终。即使台下观众已经疲惫倦怠,喝彩者寥寥,台上却无人愿意鞠躬谢幕。这个故事承载了太多人的金钱、名望和热血。一旦泡沫破灭,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的车、那么多的青春和梦想,都将灰飞烟灭。谁也不愿意摁下“清算”的按钮。
据《财经》了解,创始团队在求助政府官员,谋求上市的机会;投资人中,阿里、滴滴、中信产业基金、DST组建ofo还债委员会,进行债务重组;不少供应商同意债转股,这是他们拿回钱的唯一选择。ofo的员工们也不希望就此作散。
“风口要结束的时候,难道我们做了一场春秋大梦吗?”一位员工反问道。
对于这些缺乏商业历练的年轻人,他们在故事的开始时,往往有着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但很快,现实会教育他们。而今天的荒谬之处就在于,现实是扭曲的。
最好的时光
在2017年初年会上,酒至酣处,现场有人带头开始背诗。一位员工当场背了一首《滕王阁序》,戴威奖励1万元。
即使冷空气已经侵入骨髓,他们依然难以忘却曾经温暖而酣畅淋漓的日子。
“那是相当的rock and roll(摇滚)。”林春木(化名)于2015年9月加入,他这样评价在ofo的早期时光。这时公司不过十来人,刚从唐宁ONE小区搬至向西3公里的立方庭。对诸多员工来说,立方庭是承载他们原始荷尔蒙、野性和青春的地方。有“老三狗”之称的ofo元老——纪拓、陈正江和王耿,此时已是风云人物。他们是ofo上一个创业项目“ofo骑游”仅留的三名员工。其中,纪拓经历最传奇,他曾七次入西藏,因为太爱西藏,毕业后在那里做了一年公务员。
立方庭是临近北京大学的酒店式公寓,ofo在这里拥有一套双层复式。运营坐一楼,产品、技术坐二楼。上午,运营经理会先到城市巡查,临近午间回公司。每当纪拓回来,他总是拿起吉他,拨动琴弦,一群人跟着手舞足蹈唱起歌来。“干活干着干着就唱起来了。”
2016年初加入ofo的夏一檬(化名)说,他们经常晚上加班到10点。走出公司,一群年轻人骑公路车从海淀出发,向南至公主坟,再一路向东横穿整条长安街。接近凌晨回来,又跑到北京大学小西门吃夜宵、喝酒。一直折腾到凌晨2点才回家。
“我们这里几乎就没有超过25岁的人。”林春木有些亢奋地说,这帮人年纪差不多,爱好差不多,彼此称兄道弟;一起骑车去古北水镇,去白洋淀;聚会吃火锅——“一上来先来四十瓶啤酒,所有人必须喝醉。”
1991年出生的戴威这年25岁,刚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硕士毕业。他家境优越,父亲是国企董事长。一位下属评价他,“是好学生,但骨子里叛逆,有很强证明自己的欲望”——当年别人说他考不上北大,他考上了;别人说他竞选不上校学生会主席,他选上了。“那真是个奇迹。”这位下属认为,这两件事奠定了戴威的性格。而ofo的四位联合创始人(薛鼎、张巳丁、于信、杨品杰)也都来自北大。
这时戴威经常和员工一起喝酒。林春木惟妙惟肖模仿起戴威,喝大了站起来,右手拿烟,左手举过头顶说:“Everyone,have my word。”不过通常的状况是,喝多了什么都说不出来。
在2015年至2016年绝大部分时间里,ofo的故事始终围绕高校展开。2016年4月,它遇到扩张中第一个麻烦——已经进入20所北京高校的ofo订单徘徊不上(2万单/天)。大量社会用户和学生把车骑出校外,自行车丢失率很高。为表示不欢迎,ofo将社会用户价格从5元上调至30元,但没能把这些“不速之客们”吓退。
清明节期间,眼看着订单量一直往下掉,戴威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封校。趁着“五一”劳动节,ofo全平台暂停三天。夏一檬还记得,他们满北京城寻找失踪的小黄车,找到后拿钢丝锁把车一辆一辆锁住,标记位置,到傍晚租货车统一运回。最终,他们从校内、校外分别找回3000多辆车。与之同时,员工穷尽手段,比如到菜市场发传单、找拾荒者,最终以10元/小时的薪水雇来约50名老大爷看守校门。
封锁学校大门虽让ofo背负骂名(因学生出校活动不便),却让他们尝到了实际的商业甜头。平台重启后,北京高校单量攀升。
一个生动的细节是,有黑摩的司机不爽共享单车影响他们生意,砸ofo的车。ofo后期转化了一批相当数量的司机当修车师傅,化干戈为玉帛。
ofo此时处在双线交错的转折上。一来ofo正执行其扩张野心——它的计划是先从1个学校到20个学校,再从1个城市到5个城市,5个城市到20个城市,目前刚打完第一场战役,开始向其他城市摸索;另一方面,他们在寻求第一笔以千万美元计的大额融资,B轮往往是决定企业生死关键一步。资方对戴威的要求是:请证明你有日均10万单的能力。而整个北京高校,还只有5万多单。
纪拓建立功绩就在这时候。ofo最早拓展上海和武汉高校,认为两座城市可平分秋色,分别贡献3万单。不料上海连绵下雨,且上海学校游说门槛高,薛鼎亲自去前线督战也无济于事。而伴随5月17日营销冲单活动,仅武汉一城就贡献4万多单。武汉的负责人是纪拓。
“如果没有这4万多单我们B轮融资就很悬,当时是救命钱了。”夏一檬事后回忆。2016年9月,ofo宣布完成千万美元B轮融资。这为纪拓日后成为“雄踞一方的诸侯”提供了基础。2017年初年会,戴威颁给纪拓一辆牧马人。
也在这个800人的年会上,酒至酣处,现场有人带头开始背诗。一位员工当场背了一首《滕王阁序》,戴威奖励1万元。
钱!疯狂的钱!花不完的钱!
公司最鼎盛的时期,ofo前台都通过猎头来招。
正当ofo兴高采烈品尝封校带来的一系列胜利果实时,摩拜在上海街头崛起。因为车辆密度高,ofo在高校的运营效率令人欣羡。据员工透露,一辆车一天能被骑10次,每次5毛钱,一天挣5块钱,一个多月就能收回成本。“模型太好了,大家有点沉醉在里面。”然而,除了来自投资人的催促,2016年8月14日发生一件事,彻底激怒了ofo。
这天上班,ofo员工发现摩拜用200辆车,把方方正正的立方庭包围了。“别的地方一辆自行车都没投,明摆着是欺负人。”夏一檬至今气愤。他们商量要把这些车挪开,戴威回复说“不用”。
摩拜的举动让ofo惶恐。摩拜一辆车成本3000元,是小黄车彼时成本的15倍。他们担心摩拜足够受欢迎,更担心其背后有强大生产能力。摸不清对手虚实的ofo,当即组织人在每日凌晨3时到中关村数车。连续三天,他们发现摩拜只是把相同的200辆车,每晚装车挪到不同地方,才制造出车多的假象。而当他们悬着的心刚放下一点,2016年9月,摩拜又明目张胆挺进北大,ofo的大本营。ofo终于坐不住了。
一声令下,ofo重开校门,小黄车涌入城市。这距离它封锁校园刚刚过去四个月。从此,共享单车战场真正有了硝烟的味道。
2016年10月底,刚拿完融资的ofo将办公室搬到互联网金融中心,短暂过渡两个月后,又于圣诞节搬至理想国际大厦。这里可俯瞰北京大学,也是众多知名互联网企业云集地。在理想国际,今非昔比的ofo全面迈入大扩张、“大跃进”时期。

“热火朝天的,每天有干不完的活,当时觉得我们就该赢。”一位2017年5月加入的员工用“一场光荣的变革”来形容这种感觉。她记得入职第一天,理想国际11层人多到装不下,他们只能把一个长条桌夹在过道里,三人挤一张桌子。第二天又有人来,实在没座位,领导开玩笑说:“你坐个自行车上吧。”
向ofo汹涌而来的,除了敌人,还有金钱和欲望。公开资料显示,ofo在2016年10月至2017年7月共完成四轮融资,从C轮到E轮,总融资额超过12.8亿美元,约合88.9亿元人民币。涉及投资方包括滴滴、阿里、小米、蚂蚁金服、DST、中信产业基金等十多个明星资本。(同时期摩拜披露的融资额超9.15亿美元,约合63.5亿元人民币。)

“我们那时候觉得,投资的金额远大于我们需要的资金量。有资金积压太多,一下子使用不掉的情况。”一位ofo离钱很近的员工说,“太多了!虽然这个钱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是花得那种疯狂感……”
彼时业界公认的共享单车竞争模式是:融资-扩产能-铺车。绝大部分资金都流入自行车采购中。据《财经》记者了解,2017年3月至7月是ofo采购最疯狂的五个月。每个月采购量为300万-400万辆,总计采购1600万辆单车,实际履行约1200万辆。
一位ofo供应链人士给《财经》记者算了一笔账,那时ofo自行车单均成本360元人民币,机械锁约20元,运输物流约15元,合计近400元。换智能锁再加200元,合计接近600元。五个月总采购量1200万,乘以600元单均成本,得到这五个月的采购应付金额为——72亿元人民币(该部分尾款是导致ofo资金链紧张的因素之一)。
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人士表示,ofo当时很多部门花钱铺张。一个他们常拿来举的例子是,2017年4月ofo花费千万请鹿晗当代言人;公司为每个员工购置价值2000元的升降桌,而据一位早期员工回忆,ofo早前办公室标配是119元宜家桌子+39.9元椅子;此外,有管理层还透露过想赞助环法车队,这大概需要花费数千万欧元,当然最后没有执行。
此前财新网报道ofo管理层“一人一辆特斯拉”,据《财经》记者了解,ofo创始团队有两辆特斯拉,戴威一辆(大概率是公司所有),张巳丁一辆(个人所有)。而杨品杰的车是宝马x5。
一位和ofo有业务往来的公司高管回忆,当时和ofo有一项合作,他们说自己承担哪些费用、多少钱,ofo的反应是——“你给什么钱,这是看不起我们。”
“所有人都在抢时间。”上述人士从外部视角看,说:“就像三岁小朋友身边放了一堆金银财宝,谁都想去抢一下。他自己又不知道,别人给他一块糖,他可能就回对方一颗钻石。”比如当时,ofo的前台都通过猎头来招。
不过,在其他部门豪放投钱的时候,ofo对硬件部门相对精打细算。“车和锁想去要钱很困难,成本线卡得很死。”硬件部门员工金叶秋(化名)有些沮丧,“整个硬件在ofo的地位是很下面的。”
一位ofo公关部人士解释,这是因为ofo和摩拜是两种模式选择。ofo始终认为自己是互联网公司,商业模式、订单增长和速度为第一位,车和锁不过是完成目标的手段;摩拜从一开始认为自己是物联网公司,因而更看重硬件。
直到2017年下半年,ofo硬件矛盾此起彼伏地爆发,戴威才引起重视。一次,一批150万的智能锁因设计问题无法正常开启,戴威在专项会上发过一次大火。在场人士称,戴威一走进会议室就大声地指名道姓,相关负责人起立。他说了一些类似于“没做好”、“做错了”、“重大问题”、“工作失职”这样的话。
好消息是,2017年6月,一直处于追赶状态的ofo反超摩拜。不过,在无节制的挥霍中,戴威察觉出不对劲。2017年中的一次内部会上,戴威对在座高管说,大家的业绩和报告都很出色,但是高管对金钱没有概念,这是一件严重的事。
“所有人都在完成自己的KPI(绩效),你KPI都没达成,还替公司思考财务问题,公司先把你开了。”一位在场人士说。
在狂热竞争中,对手无时无刻都在刺激你的神经。“2017年我没有睡过一天好觉,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3点才睡觉。”一位ofo员工说。“你的大脑会不自觉紧绷,去追赶它(摩拜)的脚步,甚至是追赶前一秒你自己的脚步。”上述供应链人士说。
一位互联网创业者称,ofo和摩拜的战争很大程度陷入双方资本的盲目对冲,为了战斗而战斗,忽略了商业本质问题——“你会误以为押金是你的收入,但其实押金是你的负债;你会误以为车是你的资产,做损耗贬值,而不是支出的费用;你没想到采买成本可能是收不回来的,收回来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上述公关部人士说:“虽然心里面觉得财务模型跑不通,但觉得这么多明星资本进来,自己肯定没有投资人懂。既然投资人认可,ofo即便自己持续不下去……”他停顿一下说,“无论如何都能持续下去的。”金叶秋说:“ofo已经起来,我从没想过它能倒下。”
而一位ofo离职高层人士表示,ofo之所以用一种看似激进的姿态向前走,是因为投资人跟戴威说得非常清楚——“跑到市场第一,这是你唯一的目标,钱的事你不用管。”
2018年初的年会上,ofo请来在立方庭时员工最喜欢的民谣歌手赵雷,举办了一场以“TOP ONE”为主题的嘉年华。场上3400人,有员工感到场面一度有些混乱。也有供应商指出,这场年会费用未结清。

(2018年初,ofo以“TOP ONE”为主题举办年会,这时ofo员工3400人,过完年后陆续开始裁员。供图/ofo员工)
增长残酷物语
一位老员工说,戴威是一个在商不言商的人。
竞争的枪林弹雨已经让人目不暇接,公司内部也处在急速扩张带来的不间断权力更迭中。很多人的命运在其中几升几落、几起几伏。心态随之反复。
2016年11月,在大扩张开启前,张严琪以首席运营官的身份空降ofo。ofo迎来第一批“职业经理人”。张严琪是优步中国明星高管,因把成都带成优步增长最快的城市声名大噪。他加入ofo时,带来了一支原优步运营团队。
戴威对张严琪抱有很高期待,但他们的到来让以纪拓为“旗帜”的老员工大权旁落。在张第一次参加的内部会上,一位老员工做汇报,张严琪问了一个问题,老员工不屑地说:“这我不是讲过了吗?”戴威连忙出来调停,略带严厉地对老员工说:“你怎么这么牛呢?”
戴威对内对外多次表达对张严琪的欣赏。在2017年初的年会上,戴威宣布张严琪为“联合创始人”。另一个细节是,戴威举行婚礼,公司高管中仅请了一名伴郎,就是张严琪。
张严琪彼时带来三名管理层——范若愚接管北京,纪拓带领上十位华北骨干迁往深圳;欧竟接管上海,原城市经理被迫前往杭州;郭庆在总部负责策略。这时发生了一件在内部稍显轰动的事:原上海城市经理和张严琪因一件“小事”在群里发生冲撞,结果是这位城市经理做了辞退处理。
有员工回忆,高层当时安慰老员工说,他们也知道让这个城市经理走没太大道理,但张严琪刚来,不能让他一点威信都立不起来。这之后老员工变得收敛。张严琪团队接管一半城市,原来的城市经理均降级为运营负责人。
员工们刚开始适应这一组织变化,ofo又招了一位运营副总裁——池文明,内部人称“大池”,他曾是阿里中供铁军。大池是单枪匹马来的。按职级看,他在COO之下,在所有运营之上,但张严琪团队只听命于张。沉寂数月后,大池从外部招募一支新队伍,多来自爱鲜蜂、回家吃饭等公司。这批人接管了剩下一半城市。
ofo运营团队从开疆扩土的老员工,到陆续接管城市的张严琪、大池团队,年龄呈上升趋势。早期员工最年轻,1990年上下;张严琪的人在1985年上下;大池的人在1980年前后。到这里,ofo运营的权力交割还未结束。
2017年7月25日,伴随滴滴系三名高管进驻ofo——付强出任ofo执行总裁,柳森森和南山负责财务和市场,ofo运营体系又启动了一轮重组。就在他们进ofo前,张严琪被调去海外。付强带来运营副总裁萧双生,他与大池形成了短暂“划江而治”的格局——大池掌管中国南部,肖双生把守中国北部。他们的另一个title是“南中国区负责人”和“北中国区负责人”。
“我们这批人属于心态起伏了很多次,很多很多次。”一位ofo早期员工表示。他希望可以尽可能客观地评价这段经历——他说,老员工有抱怨,觉得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但换个角度想,我们之所以有机会打江山,是公司招不到更好的人。当公司强大,可以招揽更多更优秀人才,我们让位无可厚非。
他继续说,张严琪来时,虽然内心挣扎,但会想“是不是我们太狭隘,是不是我们太年轻才有领地意识,是不是我们职业化不够,我们觉得是一种成长”。但是后来看到一批一批人被换掉,从优步到阿里到滴滴再到阿里,特别是这些人能力参差不齐,他的想法开始转变。
心态崩塌是一步一步的。当时一位能力不错的城市经理,开始在南京,张严琪来后被调到苏州,大池崛起后又被调到无锡——城市越变越小。据一位与之熟识的人透露,大池手下喝醉酒拍着他的肩膀说:“兄弟,不是你不行,你不跟我们是一个圈子的。你到我们这个年龄你也这样。”
一位城市经理至今无法释怀,他在某城市把组装费和合作方谈好价格,他的城市被接管后,职业经理人把价格提回去了许多。“我很生气,中间差价去哪了?”甚至,职业经理人语重心长对他说:“公司好不好,再说,我们要把自己搞好。”他不仅为自己难过,为最早一起开城的200位兄弟难过,更为公司难过。
滴滴空降高管,上述早期员工的心态变了——“你们好好干,干好了上市给我分股权分期权。”而当四个月后滴滴突然大撤退——“坦白讲会有一丝幻想,是不是该我们重新撑起一片天空?”最后老板选择了大池。
这些只是运营层面。整个2017年,包括产品(CPO陈为)、供应链(副总裁杨飞)、市场(高级副总裁南楠)、人力(副总裁左佳)、财务(副总裁林叶明)、战略(副总裁黄迪),甚至客服(副总裁杜静)等,全部迎来新任高管,ofo全盘VP化。
2016年入职的ofo员工雷冬雪(化名)说,每一轮融资完都有新高管加入,所有部门都在不断空降领导。经常的状况是,一个领导来,他会招自己的团队,原有员工被边缘化,公司出现冗余。
由于ofo业务的特殊性,轻到软件产品,重至传统制造、供应链、运营,引入管理层背景混杂,包括优步、乐视、阿里、百度、腾讯、福特、沃尔玛、苹果、亚马逊、保洁等。管理挑战可想而知。
雷冬雪说,他一年都没有跳脱出空降上司的压抑心态。“有种生出来的孩子带到会走被人抢走的感觉。这孩子已经在跑,都已经跑了这么久。”特别是当新上司刚入职,拿着ofo的一纸期权递到他手里,说“你看,我给你争取到这么高的金额”时,他崩溃了。
一位VP级职业经理人承认,有时候原来的人不是干得不好,只是突然来了一拨人,他们就得把位置让开。“我当时是有点莫名其妙的。”
而一位接近戴威的人称,他曾私下表达过,“等你成为创始人,坐到我的位置上,你会做同样的决定——把不适合的人裁掉”。但后来他也表达过,自己可能信错过人。
大佬、棋子、挣扎
等锤子真的抡下来,投资人、供应商、用户,无一能幸免。但反过来说,也正是这些投资人、供应商、用户亲手将大锤交到这个孩子手里。
2017年11月的一天,一支滴滴三四十人军团突然消失。“一夜之间人全没了。”一位ofo中层人士描绘那时的震惊,“就像恐怖片幽灵船,上船所有东西还在,咖啡还是温的,但是人没了。那一片空位都没了。”他们打电话过去问,对方说在三亚度假。
对于ofo,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反抗行动。滴滴方的反击亦有组织有纪律。一位滴滴系中层人士说,付强比他们早走几天,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一起撤。“我们不走,在戴威眼中是滴滴系,滴滴这边也反目成仇。神仙打架,你只能被动接受结果。”他们约好同一天集体不出现,连东西都没拿。过了两三周,得知双方交涉告吹,才回去收拾。
上述ofo中层人士记得,滴滴的人回来办离职,笑嘻嘻地跟他们打招呼:“走了走了,江湖再见。”ofo对滴滴的态度经历了三个大转弯,三年走完了从强者崇拜,到蜜月,再到交恶的全过程。
一位员工回忆起2016年:在立方庭时,戴威每天出去见各种投资人,回到公司特别疲惫,没一会儿就趴在工位上睡着。他曾多次对内说“程维是他的贵人”。这位员工认为,这时期戴威和投资人更像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完全没有意识到博弈。
2017年7月1日,ofo做了一件外界没有看懂的事。这一天,ofo宣布成立党委,戴威当选为党委书记,联合创始人及核心高管当选党委委员。有高管称,创始人根正苗红。也有观点认为,他们的另一个用意或许是,在董事会公司治理结构之外希望再设一层决策机构,以保证公司控制权。此举表明,ofo已对股东存有戒心。
不久,7月25日滴滴高管进入ofo。据了解,ofo和摩拜正打响一轮全球范围抢人大战,恰巧部分被滴滴收购未被重用的快的员工大批外流,两家公司都在挖滴滴的人。但ofo挖,滴滴不高兴。一次戴威在内部会上说,要去跟滴滴商量一下,“如果我们不找这些人,这些人会跑到摩拜去,那还不如给我们呢”。
与之几乎同时发生的是,滴滴承诺帮ofo搞定软银的投资,条件是让滴滴的高管进来。“戴威年轻,不知道为什么让他们提前进来了,而且人这么多。”一位高管称,一个管花钱,一个管看钱,相当于“看到ofo的底牌了”。大体摸清情况后,滴滴方又抽调一批中层过来。
ofo员工中,有人感受到滴滴团队的专业(财务规则开始梳理),有人感受到流程繁琐、气氛怪异。而供应商觉得:“来了个大哥,至少以后货款能给。”
上述滴滴系中层人士的感受是,顶着“滴滴的光环”,在ofo推行的几项方案都算顺利,干得斗志满满。一位ofo员工说,人家是当做自己的事在干。
交锋发生在更高层面。一位知情人对《财经》记者表示,付强到ofo后,摆出一副要接管的姿态。高管会上,戴威很多想法他都持否定态度。其中一个例子是,戴威想收购小蓝单车,付强不同意。
小蓝单车的故事贯穿ofo始终。据《财经》记者了解,最早,小蓝名为“野兽骑行”,是ofo硬件方案提供方。当时ofo支付了一笔百万金额预付款,结果对方反悔了,不但没有把方案给ofo,预付款都没退回来。并且,小蓝推出了自己的单车业务。小蓝的态度是,我没钱给你,要不你就转股份吧。ofo在内部认真讨论了这件事,当时有人提议,“不要扶持一个敌人,必须掐死它。”然而管理层“心慈手软”。
“所有的梗都埋在这里。”上述知情人士说,去年底小蓝单车破产,ofo接管一支小蓝硬件团队。然而,滴滴却全面接管小蓝单车运营,这为后来滴滴推出自有单车品牌“青桔单车”解决了一批城市牌照问题,而青桔的存在成为滴滴谈判桌上一张王牌。“这真是一环扣一环。”
在滴滴和ofo的“蜜月期”,还有另一个意味深长的转折点。ofo接入滴滴的流量,测完发现,打车和骑车的人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骑车的人会打车,但打车的人很少骑车。“证明两轮车可以去吃四轮车的市场,四轮车养两轮车是一个新市场。”上述ofo高管说,但ofo融资条款中规定不能做网约车。
“数据出来,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事儿有多大。”林春木说,“大家都要掌握控制权。ofo不想作为盘中餐,但来不及了,它已经把脖子送给别人。”
不过,绝大多数员工对高层间的明枪暗箭并不知晓。在大部分人看来,滴滴团队到来后把ofo带上巅峰。2017年10月,在滴滴派来市场副总裁南山的领导下,以“一元月卡”和“红包车”两项活动,ofo在低迷几个月后力压摩拜。10月20日,ofo订单冲到3200万单——这是ofo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亦是整个共享单车行业的最顶峰。
整个10月,ofo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能达到目标,只要你想到就一定能做到。”一位员工描绘当时的境况。ofo立于盛世之巅,但这个盛世是“饥饿的盛世”。危险已经降临。
就在这时,滴滴、腾讯推动ofo和摩拜在年底前合并,滴滴承诺争取的软银投资迟迟没有结果,市场上出现ofo高管贪腐、合并等传言。在资本的斡旋中,对ofo致命的威胁是,新的融资没有进来。而将ofo推上顶点的月卡和红包活动,加剧了这场资金链危机。
一位接近软银人士说,当时关于软银投资ofo的新闻稿已经写好,通稿上写的融资额为18亿美元。
把付强赶走当天,戴威在内部召集临时会,通知公司要做收入——这是传递出资金不足的一次确切信号。“这之前大家一直信心满满,觉得要有一大笔融资进来,把摩拜收了,或者合并ofo占主导,或者至少滴滴占主导吧。”上述滴滴系中层人士说。
一位接近戴威的人士称,戴威事后反思,去年在融资节奏把握上过于乐观。2017年9月、10月,ofo、摩拜竞争焦灼上升,ofo占据有利地位。“那时国际资本排着队要投,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缺钱。”
ofo走到现在,身陷复杂牌局是本因——最上层是阿里和腾讯的局,中间是蚂蚁金服、滴滴、美团的局;公司治理、成本控制、创始人经验、金融环境,都是相关因素,每一个因素占一定比例,每一个因素都有量变,共同促成今天的局面。
“一个小孩去挥舞大锤,他能驾驭得了吗?刚抡起来,就扛不住了。”一位ofo供应商说,现在大家希望这个锤子能再悬一下,让阴影下的蚂蚁赶快跑。等锤子真的抡下来,投资人、供应商、用户,无一能幸免。但反过来说,也正是这些投资人、供应商、用户亲手将大锤交到这个孩子手里。
大梦一场、青春散场
“大家都在等结局,但是你以为你活到了最后一集,却一直是倒数第二集。”
在ofo搬离理想国际前的最后一个周五,《财经》记者来到ofo办公室。彼时10层、11层已在一个月前退租,15层、20层即将退租。金黄色的背景衬托办公室明亮如往昔,只是已经没什么人。满屋子堆放着打包好的纸箱,办公桌也基本收拾干净,桌面大片大片空白。ofo总部已从繁荣时的3400人裁减至400余人。才17点30分,员工熙熙攘攘下班往外走。

在搬离理想国际大厦的最后一个周五, ofo办公室灯火通明,但是已经没什么人,而楼下一层的其他公司办公区仍然人头攒动。摄影/张珺

(下图)ofo搬家前,其在理想国际20层的办公室。摄影/张珺
一位在场员工感慨,在ofo的这几年,总在不停搬家。一开始因为扩张,一层放不下,变两层、三层、四层;现在不仅从四层缩回两层,还从两三个办公场所全部集中到一个场地。而ofo给员工配备的2000元白色升降桌,在半价出售。
记者在现场看到,ofo办公室挂了两张画像——何塞·穆里尼奥和丘吉尔。两张黑色背景的海报上,分别是他们的两句名言:“早已注定,我只能在荆棘中采拾鲜花,但重要的是要对胜利和信念充满执着。”“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两句话正好代表戴威绝地重生的心境。
另据《财经》记者了解,一段时间ofo有合伙人在读特朗普自传《永不放弃》。
过去一年,不同员工的感知和内心起伏不尽相同。在大多数员工还在各种收购、合并传言中不知所措时,供应链最早感受到萧条。自去年底,ofo就在接连对供应商拉长账期,先是从一个月到三个月,后来是半年。本来在今年1月有一批尾款该支付,但ofo实在拨不出钱,供应链员工们每天忙着应对各路供应商的声讨。“我们一定会付,您再理解理解。”他们会这样说。
公关部、政府关系和地方运维在撤退前,联手为ofo打了一场反击战。面对青桔和哈罗单车进攻,ofo同时动用十几个地方媒体资源给当地政府施加压力,间接撬动地方政府让其限制投放,这使得本来准备在年初大量投放的青桔、哈罗进城时间表大幅延误。“我为我们地方团队感到骄傲。”一位公关人士说。
但ofo铺天盖地的负面没有停息过。“公关的工作是要把窗帘拉上,不让光进来,等到要宣传的时候再把窗帘打开。”另一位公关人士说,“这半年每天都在铲屎,他们还觉得我们铲屎都铲不干净。”
原先冲在最前线的线下队伍反倒清闲了,他们是裁员第一波殃及地;声势浩大的海外团队,在资金步步紧缩下死撑到今年4月,无奈开始撤离;硬件团队反应比较慢,原小米生态链总监张蕊在去年底加入后,带领团队在今年研发了一款叫“FU”的智能锁,不继续沿用“海王星”“天王星”“水星”的命名方式,是励志和ofo落寞的硬件时代撇清关系。然而,“FU”应该无缘问世了。
2018年4月4日,美团宣布收购摩拜,戴威在群里说了句“真的很可惜”。在此之前,他四处找钱试图拦下这笔交易。可惜钱找到了,交易没有拦下。
“我是很想和你把这个事玩到底,你现在跟我说你不玩了。”一位运营员工耿耿于怀。另有员工感慨:“ofo和摩拜因为没有合并,命运发生了分叉。”
5月,戴威在内部发表了一场“丘吉尔演讲”,并发起Victory计划,提出战斗到为ofo赚到1元利润。因为V计划,ofo将双休改成单休,但不久发现员工没那么多事,就又调了回来。有敏感的员工将其解读为“随着这份邮件发出,代表胜利的计划已经宣告失败”。
一位员工还记得,去年6月6日ofo两周年,公司本来说没什么钱,就不办了。但是在前几天,新的钱突然进来,两周年办得热热闹闹。而今年三周年,本来人力准备办活动让大家High一下,结果前一天被叫停。最后他们一起在阶梯教室简单听老板讲了几句,吃了个“生生不息”的蛋糕。活动上,她的同事告诉她:“我要离职了。”
这以后,裁员和离职愈加频繁。500人的离职群已经加满,现在有了第二个。群里员工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有补偿?”现在只有一小部分员工拿到。迟迟没有等到的,已经有人准备动用劳动仲裁。
“大家都在等结局,但是你以为你活到了最后一集,却一直是倒数第二集。”一位2018年7月离职的员工说。
2018年9月,《财经》记者从两个独立信源处获悉,滴滴收购ofo的交易快到最后环节,就差双方签字。ofo对供应商放风:“滴滴的钱就在路上。”很可惜,8月24日滴滴顺风车遇害案爆发,案件和后续的监管风暴一波三折,滴滴无暇顾及于此。
供应商的心态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尊重创始人的青春与热血,希望ofo能再站起来;另一方面又觉得在与ofo的合作中,他们步步退让——从开始几页纸的条款增至二十多页,但面对他们因债务陷入的惨淡,ofo态度不真诚。一位联合创始人在供应商沟通会上说:“我们也是第一次创业。”“你第一次创业,和我们要倾家荡产没关系,和全世界都没关系。”一位供应商私下反驳。
在ofo这幕历时三年的兴衰剧中,很多剧中人内心发生了巨大转折。“如果谁要是说ofo不好,我就会很难受,很后悔,甚至有点自责。”硬件部门金叶秋说着说着哭了出来。很多人把ofo今日境遇怪罪到智能锁的颓靡上。
“就算不发钱,我也愿意给ofo干一段时间。”一位90后员工说,但他还是走了,因为忍受不了部门纠缠不清的人事关系。“你可以不叫它ofo,叫of,因为没有车轮子了。它坏了,就是这种感觉。”
经历了空降上司的雷冬雪说,他迟迟不敢确认下一份工作,因为心里带着害怕、恐惧和不确定,担心“这件事会不会又在背叛我”。他说:“我们做得最错的一件事就是不够职业,我们用感情在工作。”
而早期员工夏一檬说,在ofo,450元的差旅费,他为了帮公司省钱,每次只舍得花250元。但在后期见多了贪污、捞钱、谋私利,还混得风生水起,内心不平衡。不管他未来在哪里,都会封闭情感。他正在努力成为一名真正的经理人。
当资本之手越来越熟练,创业者永远是生涩的创业者。在ofo的故事里,包括创始人在内的年轻团队不堪重负,一切都在变形。
在2018年这个雾霾席卷城市、对ofo来说尤为难熬的冬日,有一些片段是温暖的。11月28日,戴威在内部信末尾写道:“只要心中有信念,寒冬和黑暗就无法将我们打倒。”夏一檬说,只要组织需要,他随时都愿意回去。
(为保护信源,本文林春木、夏一檬、金叶秋、雷冬雪均为化名。
本文首刊于2018年12月3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经授权转载至数英,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作者公众号:财经杂志(ID: i-caijing)
转载请在文章开头和结尾显眼处标注:作者、出处和链接。不按规范转载侵权必究。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授权事宜请联系作者本人,侵权必究。
本文禁止转载,侵权必究。
授权事宜请至数英微信公众号(ID: digitaling) 后台授权,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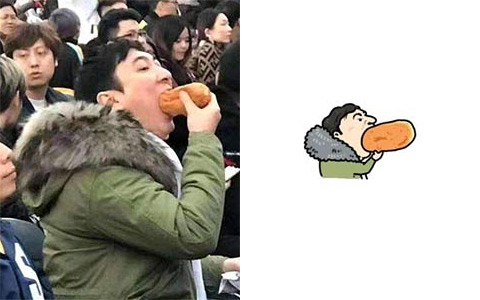






评论
评论
推荐评论
全部评论(19条)